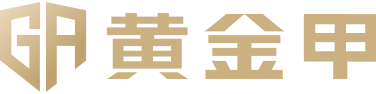反身性电影,即关于电影、关于电影人的电影,是一种需要在传统和现代主义两种语境中加以理解的电影类型。在好莱坞及其风格为代表的传统电影中,叙事结构往往被要求具有高度透明性,以使观众忽略其形式,专注于故事本身。然而,反身性电影则打破了这种惯例,通过呈现电影制作的过程或者引入叙事的不连贯性,让观众看到电影背后的机制,意识到电影之为电影的本质。
经典的好莱坞反身性电影通过展现电影制作的细节,以强调其叙事的透明性。例如,比利·怀尔德的《日落大道》不仅是关于电影制作本身,还通过角色展现了“电影中的电影”这一反身性元素。《雨中曲》和《日以作夜》同样是这种类型的代表,其矛盾和冲突都在实际的拍摄问题中得到解决。
相比之下,现代主义电影中的反身性元素更加注重形式,试图打破叙事透明性,使观众注意到影片的结构和表达方式。例如,费德里科·费里尼的《八部半》和英格玛·伯格曼的《假面》都通过在叙事中加入片段化、非线性的构造,使观众关注电影本身的形式,而非仅仅沉浸在故事中。
反身性电影可分为两种主要模式:一种是正式反身性,即展示电影制作和放映的过程和机制;另一种是个人反身性,即艺术家对自我及其创作过程的反思。吉加·维尔托夫的《持摄影机的人》和谷克多的《诗人之血》是这些模式的早期例子,分别展示了电影制作的过程和艺术家对自我内心情感与创作的探索。
正式反身性中的电影,如《假面》和《出发》,通过在叙事中展示电影制作的过程,来强化观众对电影作为电影的认知。而个人反身性电影则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和困境为切入点,表现艺术家的创作心理。
然而,与传统反身性电影不同,现代主义电影中的反身性技巧通过削弱片中人物与剧情的真实性,使观众意识到电影的人工构建。如让·雷乃和路易斯·布努埃尔的作品,他们通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,甚至将文学片段、戏剧元素引入电影,形成其独特风格,使反身性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在好莱坞电影中,摄影机、灯光、技工等因素被用来增加电影的真实性,观众被鼓励相信屏幕上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。而在现代主义反身性电影中,这些元素则被用来减弱真实性,观众被引导关注电影制作的假设性和构造本身,从而质疑电影所表现的现实。
特吕弗的《日以作夜》和费里尼的《八部半》则分别代表了传统和现代主义反身性电影。在《日以作夜》中,所有的冲突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,并在拍摄过程中得到解决。而《八部半》中,主角圭多则面临着抽象的自我困境,这些问题无法简单解决,而是关于他作为导演和个体身份的深刻反思。
通过这些电影,我们看到反身性电影不仅仅是在讲述电影制作的故事,而是在重新审视电影的本质。这种现代主义的自反项目,源于现象学的“寻找真正的真理”,强调回归自我,重新思考所有接受过的知识和经验。
无论是从哲学、文学、艺术,还是其他人文学科,现代主义的反身性都在重新定义我们的认知方式。它通过揭示过程和自我反思,挑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,使我们看到艺术的创造不仅是个体的智慧体现,也是对于自身和周围世界的不断探索和重建。